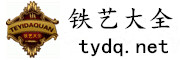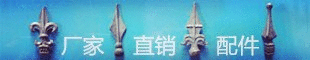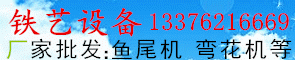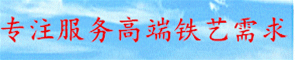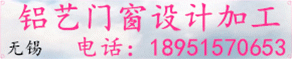三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。许多科学技术在鉴定完之后被束之高阁,没有实现产业化,没有实现技术经济价值的增值。这对于企业来说,实际上是一种损失。
四是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带头人。目前在一些企业,技术人才只是充当生产的“救火队”,在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方面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,我国钢铁行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、系统、全面、一流的科技队伍,很多领域还存在缺失、空白项目,缺乏专业、系统、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级技术人才。并且,很多企业的科技人才都在忙着维持简单再生产,没有把精力放在专心搞科研上。这种“职能错位”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科技管理体系的缺失。
五是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。(楷)科研工作产业化使得很多人向“钱”看,不愿再从事基础性技术研发,创新积极性逐渐被削弱。尤其是对于一些基础理论或共性技术的研究,如果国家支持不够,可能会出现科技发展原动力不足的危机。另外,大多数企业缺乏群众性的奖励机制和落实。现在,由于钢铁企业效益大幅下滑、压缩开支,对于全员创新的奖励有所弱化,出现了部分高级人才流失现象,须引起企业的重视。
六是多数钢铁企业没有形成梯级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计划,并且,企业为技术人员提供知识提高、补充、继续教育的能力和动力不足。比如,国家提倡企业为科技人员每年提供两个星期的学学习、知识拓展和提高时间,但这在大多数钢铁企业都没有被落实。
对于钢铁技术创新目前存在的上述问题,王维兴表示,这一方面与当前钢铁行业全面陷入经营亏损息息相关,另一方面与钢铁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完善有关,需要企业尽快转变理念,重视科技创新体系建设、完善。
“七建议”指引创新体系发展方向
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,是国家和企业的命脉,绝不能因为经济效益下滑而丢掉了长远的效益。对于未来钢铁技术创新体系的发展方向,王维兴表示,要积极探索体制和机制的创新,以经济效益为中心,解决当前影响生产经营的关键问题,依靠技术创新来扭转亏损。他强调,推动技术创新有助于解决钢铁工业降成本、保盈利、稳市场的问题,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。
第一,对于科技研发项目要区别对待。对于共性、重大、基础类、前瞻性研究,国家应给予必要的支持,或者由行业牵头,通过组建技术创新联盟、产学研联合攻关等方式,优化资源配置,实现协同创新。对于那些可以进入市场的技术研发项目,要鼓励其进入市场,参与市场竞争。
第二,要鼓励跨行业、跨单位的产业链联合研发,加强协同,继续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向深层次合作发展。对于重大技术问题,应该建立集各方资源和财力于一体的重大项目的立项研究,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行业来考虑。比如为适应造船行业新标准的要求,应该形成从钢铁产品生产到造船的设计和应用相互衔接的研发团队。同时,要继续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研发模式,通过合作研发、有偿转让的方式,充分利用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的技术资源,提高技术创新的前瞻性和效率,直接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。
第三,要重视对科技成果的评定,注重后续的成果转化、跟踪和评定。在评定科技成果时,建议加上该成果应用产业化的程度这一项内容,通过后续评价来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。另外,可以考虑扩大专利的使用范围,扩大成果的应用,实现科技成果价值的增值。
第四,鼓励企业建立技术服务公司,打造技术创新服务队伍,延伸产业链。这一方面可以成为钢铁企业发展非钢产业的重要经济增长点,为企业提供一个技术孵化和创新的平台,为下游用户提供科技服务;另一方面可以留住人才。
第五,要建立与企业技术发展程度相匹配的奖励机制,并且重在落实。例如,宝钢每年会拿出几亿元奖励科技人才和合理化建议。根据宝钢的经验,一项创新为企业带来的效益是企业奖励该项创新金额的10倍。因此,企业因为效益下滑而压缩技术创新费用是得不偿失的。
第六,对于技术创新的考核要讲究经济性,不能单纯追求指标的优化。企业开展技术对标要务实,建立一个宽松的、公正的、实事求是的指标体系,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原则地开展,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,而不是追求某一个单一指标的先进。
第七,要重视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,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。现在,宝钢、武钢、鞍钢、首钢等大钢铁企业已经形成了梯级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立体系,但大多数钢铁企业在这方面还处于缺失或刚刚起步的阶段。建议企业间要广泛开展科技技术信息交流与合作,为技术人才提供一条持续培训、互通有无的渠道。